具体到当前业内各种各样的现象,一个有悟性、愿意不断提升自己的人,一定要有超乎普遍水平的认知,不要人云亦云,盲目跟从,要有自己的主见与判断,尤其是,要使这判断经得起检验。此底气从何而来?当然是来自对经典的学习,来自丰厚的视觉记忆,来自朝朝夕夕的思考与磨砺。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如果划地为界,局限于某一特殊门户之内,则对此门户本身也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那么同样,盆景人的目光如果仅仅局限在盆景这个小圈子内,不能站在文化艺术这个广阔的背景中去比较衡量,也无法获得对盆景的清晰认知。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诗句脍炙人口,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苏东坡之所以可以超越他的时代,成为震铄古今的大文学家,就在于他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在词曲歌赋中,他晚年在《答苏伯固》中有言:“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就是这看似与“文学”关联并不紧密的《易经》、《尚书》、《论语》三本书,占据了他心中重要位置,他曾殚精竭虑为此三书作传,并极看重这一成果。这就是一位大文学家的深厚学养和宽阔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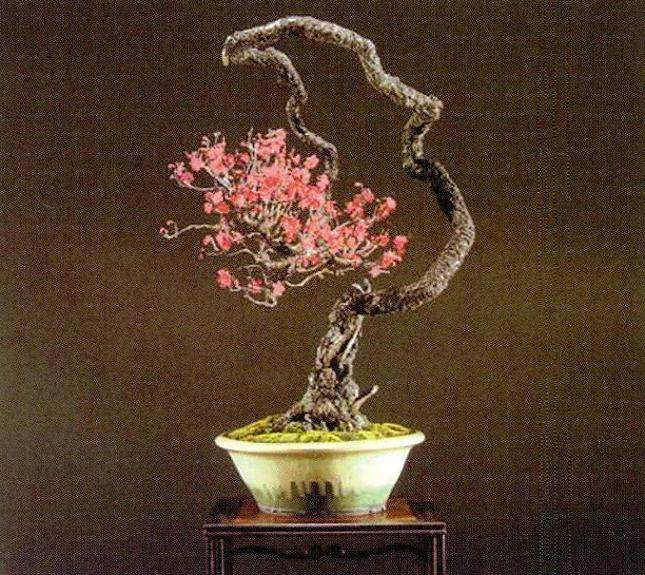
使徒保罗说:“看得见的东西是被看不见的东西主宰的。”此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个著名的“冰山一角”——更多修炼和深意潜在水面之下。
任何领域、任何人,如果不能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不太可能“成一家之言”的,起码我对他发出的言论保持怀疑。原因很简单,前面也反复说过:你的思维还没有与古往今来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沟通联结,你的心灵和曰光还没有被它们浸润锻造,你还没有形成最基本的参照系统,所以,你的意见连“一家”也难称得上。遍知百家,方有可能成为一家——您知百家么?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结论,都要放在历史与人类已知的文化成果中碰撞、衡量、比较、对照(这也是上文提到的“跟谁比”的问题),“论从史出”说的即是这意思。只有这样,此“论”才有可能经得起时光冲刷,屹立不倒。 由此反观盆景圈内的评比与鉴赏,指鹿为马者比比皆是,尤其身临展会,看到那么多平板呆滞的作品被挂上金灿灿的奖牌,不禁直眨眼睛,也不知该说什么好,甚至有那么一会儿,蹙眉搔耳,一头雾水,不过很快也就舒眉展颜,心下释然了:难怪这个艺术门类一直走不进更高的艺术殿堂,不能吸引更深刻精准的目光,原来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们对美的法则就存有深深的隔膜啊。
“……不要说别人看不懂、不理解,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怎么会缺少锐利敏感的目光呢?问题是,你能不能让这样的目光被触动。还是要从自身找问题,这是一个理性清明的人应持的基本思路。”(拙文《自然与工艺》片断)。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跟他们视野偏狭有关。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生中只围绕着盆景打转,很少将目光移向其它领域,即便有所涉猎.也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满足于知识层面的了解,并没有被其真正感动过,更不要说沉迷、追随了,因此无法领略那些杰作的精妙和美好,也无法积累起对于“美”的敏感和经验。说来好笑,终生致力于盆景,到头来连盆景的好坏也拎不清楚。 这恰好可与钱穆的论断相印证。
在禅宗,最重要的就是见地。看似简单的一个判断,其实是以他的全部学识与才华为依据的,一语即可见这人的全部“家底”。也就是说,此人的知识、阅历、悟性、直觉、洞察力等等,在这句话中一览无余。所以古人说:“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木心说得好:“你听了莫扎特,说好,又听了河南梆子,也说好,那么你前面的话是假的,你不懂莫扎特。”
以我的经验和观察,一个人把不好的作品认作好,那么,当真正的好作品摆在他面前时,他会认不出来。这一点,屡试不爽。即便有时看别人眼色也跟着拍手,那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盲目跟从罢了。 班乃特在《经典如何产生》一文中指出:一部作品所以能成为经典,全是因为最初由有三两智勇之士发现了一部杰作,不但看得准确,而且说得坚决,一口咬定就是此书,而世俗之人将信将疑,无可无不可,却因意志薄弱,自信动摇,禁不起时光再从旁助阵,终于也就人云亦云,渐成“共识”了。
有感于此,作家余光中说:“一位杰出的评论家不但要有学问,还要有见解,才能慧眼独具,识天才于未显。更可贵的是在识才之余,还有胆识把他的发现昭告天下:这就是道德的勇气、艺术的良心了。所以杰出的评论家不但是智者,还应是勇者:” 撇开勇气不谈,在这里,我们重点说说如何获得“智”?
这个问题看似很大,而要作出回答又很简单:学习。 “好学近乎智”嘛。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学识”。学识,顾名思义,由学习得来的知识或认识。也就是说,通过学习,获得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进而获取对事物准确判断的能力。任何领域的鉴赏,学识都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上面说到的“参照系”,便是由学而来。大鉴赏家,即便不是大学问家,也是学识极其丰富广博的人。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好像与以上言说存在“冲突”,那就是,在我们的经验里,可以看到某些人(当然,比例极少)并不具备丰厚的学养和广博的知识,但是他对一些作品的判断非常准确,或者说他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创作家,并且也做出了令人击节的作品。这样的人,无论现实还是历史,从来不乏其例。
个中原因较为复杂,但若以简洁的语言道出原由,那就是:禀赋使然——他在造型上有着常人不具备的敏感,一生痴迷、专注于此。比如我国民间剪纸,其中很多作者连字也不认识,更谈不上接受正规教育,但其作品中却体现出了非凡的想象力和绝妙的艺术才华。正是由于这些人的特殊禀赋,使其面对一些艺术作品时,常常能一语中的,道人所未见,而且许多观点异常深刻。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我就遇到过不止一位,也是从他们身上,我深受启发和教益。
但与之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即便他们拥有出众的创作才华,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作品的判断一贯精准,有时候他们的一些观点、结论又缺乏起码的常识,使人大跌眼镜。对此我也进行了思忖:这是因为,一旦有的作品与他的生活经验、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不相符合,那么近乎本能地,他会排斥与拒绝。说到底,还是他认知系统、理解能力和审美趣味不够宽泛、广博的缘故。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评论界提出一个观点,叫作“深刻的片面”——与萁肤浅地泛泛而谈,不如凭藉一己思悟和生命体验达致局部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向我所认识的前辈、朋友致敬。
还是回到了“学识”上。无法想象一个有着出众创作才华但学识较为贫弱的人,会成为趣味宽泛、理解深入、认识全面的鉴赏家。当然优秀的鉴赏家也离不开“形式天赋”,否则当他遇到杰出作品时会无法辨识,这“辨识”的结果,即是他在丰厚知识储备和敏锐目光的双重合力下,将“发现”的喜悦及时倾吐,呈显为文字。
在书法、绘画、雕塑史上,理论、创作、鉴赏三栖的一流人物比比皆是。理智与感性的相互激发,会使其成果愈发璀璨恢宏。当你深入一位伟大艺术家时,便会发现,他对这个世界有着极其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具有无尽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正是这些,才促使他不断学习也不断创造,一步步走上了艺术的巅峰。正所谓“非学无以广才”,学习,促英才能愈发广大。
万众崇仰的释迦牟尼佛有十个名号,其一为“正遍知”,即正确地遍知一切事物。何以能够如此7当然是由学而来,而且佛陀的学习更是历经干辛万苦,累世积劫。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回答有千万种,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清晰认识自己,获得智慧。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无法正确认知的话,我们又怎能相信他对别人的剿断呢?
“自知者明”,此语颠扑不破。 这也是认识世界的起点,一切都从这里起步。
圈内常会遇到一些人,对自己的作品出奇的自信,很少有审视、旁观自己的能力,仅从这一点观察,对其言论就不禁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仅仅从他对自己的判断中,我们就觉出了偏差甚至错谬,那么他往下的言说似乎也无倾听的必要了。
人,每时每刻与自己厮混,真正的“全方位”、“零距离”、“无缝隙”,如此,还不能给自己一个恰切的评定,谈何看清自身以外更复杂的人与事呢?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历古弥新却又无时无刻不环绕我们生活的一个问题:智慧。关于这个词,净空法师作过这样的诠释:“智有照见的功能,慧有鉴别的作用。”此语移到盆景鉴赏领域,纤亳不差:在对一件作品观照、审度以后,能否做出准确的鉴别与判断,又何尝不是检验一个人专业智慧的试金石呢? 盆景鉴赏,看似一个较小艺术门类中的一个小小环节,若真正跻身艺术批评的行列,就无法回避鉴赏者自身素养的问题,往深了说,要看他对世界、对艺术、对自己的理解是否深入、正确。
而这,就与一个人的“智慧”密切相关了,也与人类整个文化艺术成果紧密相连。 看来,沿任何一条小溪往上追溯,都可以走到大海。 具体到当前业内各种各样的觋象,一个有悟性、愿意不断提升自己的人,一定要有超乎普遍水平的认知,不要人云亦云,盲目跟从,要有自己的主见与判断,尤其是,要使这判断经得起检验。此底气从何而来?当然是来自对经典的学习,来自丰厚的视觉记忆,来自朝朝夕夕的思考与磨砺。
我国传统典籍《中庸》,对“学”与“辨”有过极精彩的阐述,不妨将之引申到盆景鉴赏: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却精准道出了为学的路径和步骤:广泛地学习,仔细地探究、审慎地思考,明晰地辨别,坚定地落实。而“博学”,就是鉴赏的筑基阶段,越过这一阶段,“明辨”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沙上建塔并无二致。所以,若想练就一双慧眼,获得明晰透彻的辨识能力,只有打开视野,充实自己的头脑和内心,使之愈加丰富、深邃和广阔 没别的办法。
除了学习,我还想说的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一个有着明彻目光的人,一个敏于感受的人,是不可能对大自然无动于衷的,相反,他会深深地沉迷和眷恋,他会在大自然面前无端地激动起来……因为,它不仅仅是艺术和思想的生发之地,也是一切的源头和归宿。这其实,也是鉴别一个艺术家的有效方法——真伪与否,看看他在自然面前的态度就知晓了。
(缟辑/古丽)
